长安内外:唐代京城书写文化的东西流行:敦煌学新视角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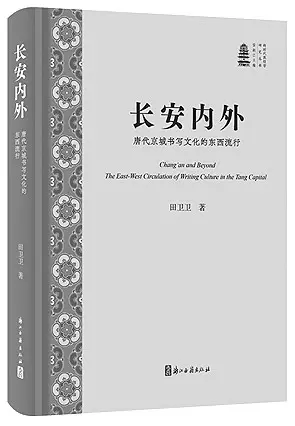
《长安内外:唐代京城书写文化的东西传播》田卫卫 著浙江古籍出版社
如今,敦煌学已经走过一百二十年的发展道路。郝春文在《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一文中明确指出,除了传统的文献学和历史学方法之外,敦煌学的研究还出现了写本学、社会学、叙事学以及传播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并且开辟了文书学、书籍史、知识史等新的研究方向,其中一些已经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田卫卫的作品《长安内外:唐代京城书写文化的东西流行》,是借助“文化流转”这一新颖角度,剖析中古时期书写文献的独创性研究。这部作品从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选取了敦煌文献和日本古代文献里具有代表性的长安书写文化文本作为研究重点,通过细节展现唐代都城书写活动在不同地域间的传播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延续,描绘了书写行为作为文化传递手段的演变过程。
这本书的上部分名为“从长安到敦煌——韦庄《秦妇吟》的流传与记录”,选取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了以长安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敦煌地区的传播状况。《秦妇吟》的研究历史几乎与敦煌学的发展同步,是受到关注时间最长、吸引中外学者最多、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敦煌文献之一。该书作者不局限于文献学、文学、艺术学等既有研究角度,而是运用写本学和传播学方法,全面考察藏经洞出土的每一份《秦妇吟》文献,逐条分析写本特征,借由文本与细节,阐明《秦妇吟》写本的创制与流传轨迹,尤其对《秦妇吟》在敦煌地区的流传途径、接受群体、影响广度及其具体效应等议题展开深度探讨。在S.5477与P.3910号写本的比较研究中,在分析韦庄为何自我限制《秦妇吟》的背景时,作者还呈现了若干值得重视的全新阐释,这些观点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秦妇吟》的理解深度。
下编以“长安及其文化关联的敦煌、奈良的书写研究”为题,将研究范围拓展到西域敦煌的寺学以及东瀛奈良的宫廷体系。通过考察敦煌学领域的书生研习《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的碑帖,并分析日本皇室摹写的《杂集》、王羲之《乐毅论》等作品,揭示唐代都城书写艺术在国内外的影响轨迹。依照作者在书中的归纳:起初是通过不断练习单个字符来掌握文字的基本技能,接着是研习经典著作以获取知识,而后又涉及宴饮礼仪等社会交往的习俗,这些唐朝典籍文化传入日本后,在当时的读书人群体中广泛传播,对他们的日常行为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作用,进而对社会整体氛围带来了诸多积极改变。
通读下来,该著笔酣墨饱,慎思明辨,具备三个显著特点:
这个作品考察范围非常宽广,它对文明之间的互动与借鉴有明确的认识,虽然主要讨论敦煌的文献资料,但研究范围延伸到了丝绸之路的起始地长安,又虽然分析日本的古写本,却将考察的目光追溯到大唐时期,作者把敦煌文献和日本古写本放在文化交流的宏大环境中,勾勒出了长安文化的流传路径。他的眼界宽广,还表现在资料使用上的不拘一格——除了敦煌文献,还把石刻墓志、正仓院文书、木简文书都包含进来,实现了“超越敦煌文献研究敦煌,避开日本古写本研究奈良”,为“比较写本研究”树立了典范。
这项研究在方法论上十分恰当,中古时期的写本文献并非静止的实物,而是流动思想的表现形式,研究者同时关注写本的实际形态、文本特征以及社会背景,借助严谨的文献考证和有说服力的历史分析,将各个文本所蕴含的信息和文化意义都全面地呈现出来。更令人称道的是,作者通过分析写本中的重复符号、朱墨标注、增删记录、字体风格等书写特点,推断出书写者的具体身份,同时依据装帧方式、纸张尺寸颜色、行文格式字数、题字随笔、物品清单变化、抄写纸张类型等线索,确定了文献的流传路径,整合了信息来源、传递者、阅读者、载体形式等关键要素,阐明了长安的书写艺术如何借助陆上与海上通道传播到中亚地区,并远播海外的发展轨迹。多维度甚至跨学科地进行写本学研究,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第三点,事例形象,分析恰当。比如《秦妇吟》的抄本、《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的拓片等考证,主要关注我国西部边疆的读书人,而《乐毅论》《文选》《古文尚书》《盛唐诗》东渡的研究,则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日本奈良王宫。作者以“文化传承”为脉络,选“亲笔记录”作骨干,取“誊写复制”为辅助,把看似孤立的实例连缀成串,节节相连,构建出长安文明在草原丝绸之路繁盛多彩、持续发展的互动体系。尽管长安城因朝代更迭而经历兴衰,但长安文明借助典籍作为媒介,在众多群体的推动下,在域外文化环境中茁壮成长、绽放异彩。
总之,作者以长安作为基准点,将唐代文化向四面八方传播的轨迹,用精确且形象的语言进行了阐释,他宽广的见识、独特的角度,为运用新思路、新手段拓展敦煌文化研究新天地,作出了具体的说明。
(作者:宋雪春,系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